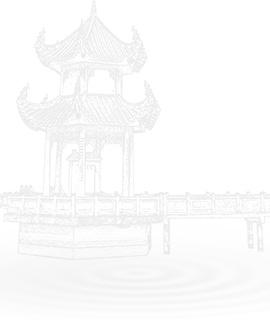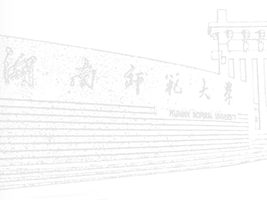2024-12-04 16:49 來源:紅網 作者:譚偉平 點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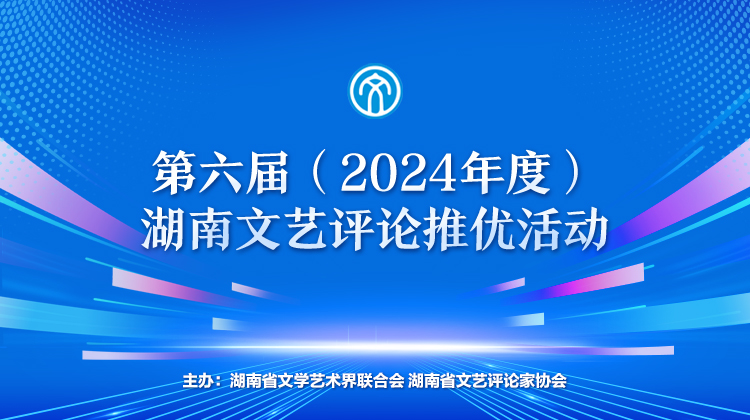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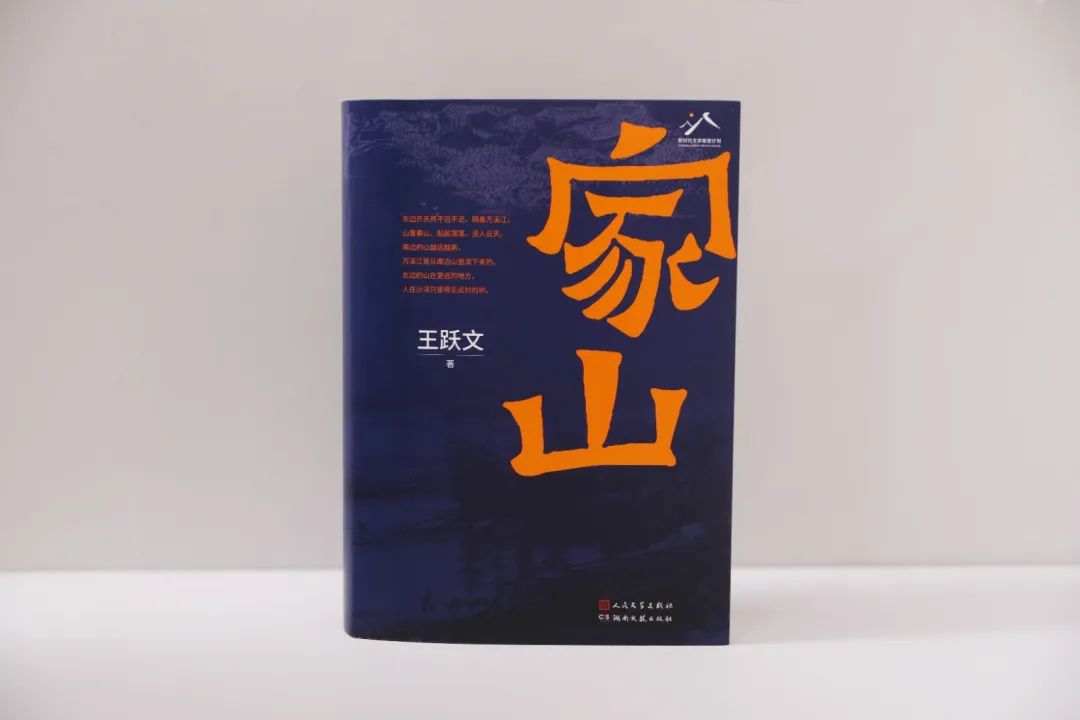
《家山》的精神基因與藝術特色
文/譚偉平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史上,鄉土文學中的家族小說占據了很大的板塊。王躍文的新作《家山》,以中國南方沙灣村陳家五代人為切口,將中國鄉村近百年的歷史風云徐徐展現出來,草蛇灰線般描繪了華夏民族現代百年歷史進程,是鄉土中國文學或家族小說的新收獲,可以謂之中國鄉村百年變革的歷史教科書和民族史詩作品也不為過。作者以自己的家鄉為觀察點,在文學的原鄉、原地、原點創作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與創新,將中國鄉村的民族基因與精神底色,藝術地勾勒出來了。這部小說,與王躍文其它小說相比,有著迥然不同的敘述特色和藝術風格,小說用風輕云淡的口吻,在看似波瀾不驚的敘述中,卻將中國民族基因與精神底色和盤托出,體現出中國鄉村無比強大的精神力量。
一、賡續傳統基因,彰顯大義美德
站在時空的結合點上,以中國鄉土和中國家族內容為創作母題的優秀小說很多,而王躍文的新作《家山》,卻獨辟蹊徑,作者以湘西一個山村為切入點,以新時代新視角為歷史背景和創作出發點,以家鄉的歷史演變為觀察原點,通過大量的典籍考證與研究,對家鄉的生活歷史與倫理邏輯,做出了自己新的書寫與思考。
作品中用相當篇幅描述了兩個“大辦”:大辦水利(紅花溪水庫)、大辦教育(沙灣國民初級小學),這其實也是這部小說的兩條敘述結構主線。既體現了耕耘為本的傳統基因具有非常強的生命力,又體現了教育興村的經濟之道和文化文明之導向。
小說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不是簡單重復耕讀傳家的動人故事,而是站在歷史文化發展的高度上,寫出歷史背景下耕讀傳家的新舊之爭與新舊之變。舊的田賦制度不合時宜,雖然幾經變革,仍然捉襟見肘,不堪重負,只有徹底的革命,才有新的生機。舊式私塾教育,也不能起到啟蒙的作用,只有新式的教育體系,才能培育創造充滿活力的新人。在傳統的形式上進行新的挖掘,在耕讀傳家的歷史長河里,寫出舊路(舊制度舊秩序)的千瘡百孔、蹣跚踉蹌,描繪新路(新人新事)的曲折與頑強。正如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一樣,教育是國民的命脈。大興水利與普及教育,都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小說以這兩大主脈為結構線索,去組織故事情節,臧否人物對錯功過,評判歷史是非曲直,認識傳統文化長短優劣,為未來留下了寶貴的藝術圖鑒。
1.突出重教本色,維護家族榮譽
沙灣國民初級小學的成立,不只是沙灣村民政治文化教育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鄉村發展的一個縮影,是中國傳統文化重教本色在鄉村中的生動體現。由陳劭夫題寫的辦學碑文,開章明義寫道:“國家之強弱,關乎國民識字之多寡。是故有識之士,莫不以廣興學校普及教育為目前救國之急務。”(《家山》第256頁) 教育關乎國運,關乎子孫后代,關乎未來,已成共識,也是維系中華民族的根基之所在。一個家庭、一個村落、一個宗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薪火相傳,興旺發達,與教育息息相關。《家山》以小說的形式,形象地闡明了教育在中國鄉村的重要意義——教育才是家山的重要基石。
家教家訓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家族榮譽幾乎是家庭成員與生俱來的本能,是溶化在血液中的自覺行為。《家山》在這方面的描寫也是十分突出的。如為家族增光添彩的劭夫,成為沙灣村人人景仰的大英雄。劉桃香闖進縣衙門贏了官司,讓眾人佩服,被譽為“鄉約老爺”而美名揚天下。而身為知根老爺的陳齊樹,因為兒子五疤子坑蒙拐騙,成為沙灣村人人避之的“另類”,讓他在村子里抬不起頭,也給其家族蒙羞。
在《家山》里,體現了多以規勸、教化為主的傳統文化方式,凸顯出道之以德,以德化人;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的思想文化基因,從而使《家山》染上了敦厚恭儉的文化基因原色。
2.彰顯大義美德的家山倫理底色
《家山》通篇彰顯的是中華民族的大義美德,我們可以從佑德公、逸公、有喜等人物身上,探視到民族傳統美德的波光粼粼,小說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中華傳統美德的博物館。
近現代中國所出現的苦難與危機,在《家山》中均有反映。作品在描寫這種苦難與危機的同時,更是表現了人們抱團取暖、扶危濟困、生死相依的大義美德,如作品中描寫沙灣村眾人對抗戰出糧出物的踴躍;對洪災過后相互救濟的描寫,都感人至深。這在很大程度上傳承了的是中華民族的道德基石,是中華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延綿不絕的重要原因。扶危顯大義,濟困是美德。
從《家山》里,作者還巧妙地在扶危濟困的描寫中,將對弱者的同情轉化為對革命的向往。比如齊峰初建革命武裝遭到圍剿時,沙灣村民將村中的“紅屬”護送到山里保護起來;齊峰假死時家人及村民對他的態度;佑德公從帶頭積極完賦稅支援抗戰,到后來帶頭抗糧抗稅等等,這些故事描寫,真實自然地表現了當時的民心向背與歷史潮流的發展。
《家山》是用人物的行動與語言,來表現這一倫理底色,如作品中寫道:沙灣流行不少典故,“坐得黃包車,顛得屁股腫”是說人不要貪圖和自身不匹配的事物, “拖檐底下定規款,見不得人”是諷刺只顧個人利益的、不一碗水端平的人,作者用這種沙灣人獨有民間俚語來形容、議論和評價人,既充滿了詼諧風趣,又形象生動地體現出民間“識好歹、知善惡”的倫理評判標準。讀來在會心一笑中非常容易接受和認同這一民族共識。
書中既有出身教師的向(遠豐)鄉長、朱(顯奇)縣長這樣有道德淪喪的冷色人物出現,也有逸公、佑德公、有喜等這類近乎道德完人的暖色人物塑造。他們的造型都染上了濃厚的道德取舍,這種道德取舍既有強大的傳統文化基因,也具有濃厚的民間倫理底色,它也是傳統鄉村治理的調色板,在民間具有很強的約制力,是維系鄉村秩序不可或缺的隱形手段。
3.呈現出親情友情為最大財富的意識
中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是仁義禮智信,在這背后支撐的最根本的基石,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親情友情。以各種血緣姻緣關系扭結在一起,組成了中國最基本的社會結構。在《家山》里,徐徐展現的,就是這一亙古未變、亙古難變的社會結構圖。
作品開篇寫四跛子陳修權殺外甥引發的官司,以及后來讓桃香生的兒子過繼給姐姐家,以及佑德公對家庭與家族竭盡全力的維護;逸公對弟弟一家“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式的寬容,都是這一意識的折射。
作品對陳有喜這一人物的刻畫,是小說所表露出來的視親情友情為最大財富的集中體現。這個形象的塑造,是以往作品中沒有的,填補了現當代文學形象塑造的空白。
陳有喜出身低微,八歲就來到佑德公家,跟著佑德公做事認字算賬,名義上為佑德公家的長工,實際上成了佑德公家的管家。他頭腦靈活、慮事周到,一人可當幾人用,佑德公并不將他當作下人看待,而是視為家人,小到開抱棚,大到主持婚喪嫁娶,大小一應事宜,均放心交給他去料理,這還不夠,干脆將有喜認作自己的孫子,并通過聯姻成為姻親家人。有喜雖然離開了佑德公家,但他仍然心掛主家。他對主人家及沙灣村的全力幫助與維護,贏得了全沙灣村的一致認同。所以才有后來揚卿推舉他擔任紅花溪水庫修建的總指揮,他也不負眾望,圓滿完成了這一工程。可以說,有喜這個人物是《家山》人物譜系中最具傳統亮色的形象,他的出現,彰顯了傳統文化影響力的強大!后繼有人是刻入中華文化骨髓的元文化,那么,視親情友情為最大財富也就理所當然了。
二、一葉而知春秋的乾坤筆力
《家山》的筆力主要落在一個較為偏僻的湘西沙灣村,但我們從書中完全可以感知到時代的波譎云詭,由此可見作者掌控長篇小說結構的高超水平。
1.從一村一隅窺社會風云
有人認為:“王躍文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的作家,在新時代的歷史背景和新視角下,返回時間深處和歷史深處的家鄉,對家鄉中傳統的生活與倫理做出新的書寫與思考。”王躍文也反復多次提到:“深刻認識到鄉村是最大意義上的中國”。因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在鄉村,鄉村之中蘊含著豐厚的精神資源值得當代人去重視和挖掘。無論我們走到多遠,見識多么寬廣,都不能也不會忘記曾經出發的鄉村。小說敘事的范圍雖然沒有超出一個縣,而落筆主要在一個村——沙灣村,但我們能從中可以感覺到時代風云的激蕩變化。一葉而知春秋,這既是小說的邏輯切入點,也是許多評論者所贊譽的“史詩品格”。
2.從一族一家察世風變異
《家山》主要寫了沙灣陳家五代人:遠字輩逸公、達公、放公,揚字輩揚卿、揚高,修字輩修福(佑德公)、修根、修權(四跛子)、修碧、修岳,齊字輩齊美(劭夫)、齊峰、齊樹、齊岳,有字輩有喜、有仙(五疤子)等,在這些人物描寫上,個個都富有代表性,或者是階級、階層的化身,如佑德公、齊峰、有喜等;或者是時代精神的化身,如逸公、齊美(劭夫)、桃香等;或者是宗族家族的化身,如揚高、齊樹、朱達望等。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精彩的故事,但小說著墨最多的是三個人物:佑德公、揚卿、齊峰,他們代表了三個階層,走的也是三條路徑。
在這樣一個家族高度集中的族群社會里,彼此之間都知根知底,為人行事都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每個家庭及代表人物在時代風云激蕩中,都打上了本家族的時代社會烙印,如逸公的豁達明理——作為前清的知縣,不問世事卻關注社會;揚卿的執著堅定——修水庫辦教育,成就他信守技術報國的夙愿;佑德公的仁義樂善——是沙灣村實際的主事人,鄉賢中修行道德的楷模;齊美(劭夫)、齊峰的革命精神——藝術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會誕生并在中國迅速發展壯大的原因……小說雖然落筆于沙灣村,寫的大部分都是家長里短、煙火人生。但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與重大的歷史事件直接關聯著,可以說,家國同構的關系在小說中得到了形象和直接的展現。
3.從一賦一征看鄉村治理
在《家山》中,雖然也出現了六任縣長及鄉長、保甲長們等肩負鄉村治理的官吏們,但“治理”的主要內容就是征糧與征兵,小說寫佑德公拜見多任縣長,通過佑德公的言行觀察與心理活動,透過一賦一征,寫出了政權更迭的歷史必然性。如他為縣長李明達出主意“賦從租出”,為此出臺了《倡議書》,完成了一次稅賦征收改革,但利弊互見。小說寫佑德公從帶頭積極完賦交稅支援抗戰,到后來帶頭抗糧抗稅,其中故事值得玩味,從側面反映了病入膏肓的腐敗政權無法逃避的滅亡命運。
4.從一山一水知時代更迭
在《家山》中,有一段描寫,寫揚卿回憶他們三個小伙伴在萬溪江游泳的情景,看近知遠,寓意深遠,三個當年的小伙伴,后來都成了沙灣村走出來影響時局的大人物。
王躍文在談創作體會時說:“正像佑徳公家娘井的水會流到長江和東海,沙灣村父老鄉親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酸甜苦辣都連著波譎云詭的時代和災難深重中浴火重生的中國。我力圖把這部小說寫得扎實、豐富、遼闊,追求我理想中的史詩品格。”齊天界的抗日武裝的組織,后來奠定了湘西縱隊的基礎。從小在萬溪江水里泅水的三個小伙伴:揚卿、劭夫、齊峰,隨著時代的推進,都成長為社會的棟梁。萬溪江猶如寓言般地見證了時代的變遷,萬溪江匯聚了涓涓細流,奔向沅江——長江——東海,小說通過描寫萬溪江,演示了萬川歸海的歷史發展規律。
(節選自第六屆(2024年度)文藝評論推優活動文章類優秀作品譚偉平的《<家山>的精神基因與藝術特色》)


譚偉平,博士,二級教授,湖南省教學名師,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懷化學院原院長、黨委書記。現為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會會長。出版專著5部,主編教材4部,發表論文200余篇。先后從事過文學評論、影視策劃、歌曲創作、藝術評論、散文寫作,以及文化旅游策劃等。近幾年在《人民日報》《文藝論壇》《湘江文藝》《紅網》《湖南日報》等報刊媒體發表了《傳遞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和光同塵 與時舒卷》等數十篇藝評與游記散文。
原文鏈接:https://moment.rednet.cn/pc/content/646856/96/14512045.html
【關閉】